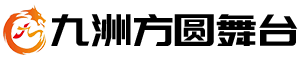他為中國新藥研發行業所貢獻的,遠不止一家總市值千億的集團化企業。
中國醫藥行業正迎來多層次的深度變革。
5月1日起,國內進口的抗癌藥正式實現零關稅。同時,通過對已納入醫保的抗癌藥實施政府集中談價、采購;對未納入醫保的抗癌藥實行醫保準入談判等措施,抗癌“救命藥”的價格有望大幅降低。
市場變化的同時,醫藥企業也迎來新的機會。資本市場改革中,“支持優質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的核心理念,被認為十分契合有志于研發的醫藥企業。
此前很長時間內,融資難被認為是中國“新藥”難產的命門之一。新藥研發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而一旦成功,往往意味著巨大收益。在美國,不乏產品停留在臨床試驗階段,便登陸資本市場籌措資金的初創醫藥研發公司。而在A股,由于各項“硬性準入門檻”,這類醫藥公司常年與資本市場無緣。
新三板的開放,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一批醫藥企業解決了研發資金難的問題,而A股的改革,則被認為將為有實力、有國際抱負的醫藥企業提供更廣闊的機遇。
行業翹首以盼更多中國“國際級新藥”之際,一家專門服務于新藥研發的巨頭公司,已正式返回。
藥明康德,作為中概股回歸IPO第一股,還未完成上市,已博得廣泛關注。這家與輝瑞、強生、羅氏、禮來、默沙東等緊緊捆綁的CRO/CMO企業,將給中國新藥研發帶來怎樣的變化?
21世紀初,在歐美醫藥界和風投人眼里,中國不可能誕生新藥研發外包服務公司(CRO),至少不會成為一個行業,因為中國不具備這樣的研發實力和基本土壤。
2007年12月,來自中國無錫的新藥研發服務公司藥明康德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給唱衰之人以重重地回擊,引發國內外業界和資本市場轟動。
彼時,在紐交所掛牌的大中華地區企業有40多家,藥明康德是第一家靠腦力提供研發服務掙錢的企業,被稱為“華爾街首次為中國的頭腦買單”。
藥明康德不僅成了中國新藥研發服務領域世界第一股,也被業界認為是中國CRO行業的拓荒者。
CRO是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藥物臨床試驗合同研究組織)的簡稱,通俗理解為承接制藥企業研發業務的公司,上世紀70年代最早出現在美國,是制藥業激烈競爭的產物。
在接下來的20多年里,新藥研發難度加大,周期延長,制藥企業為減少成本、加快研發速度,將越來越多的研發項目交給了CRO企業。CRO逐漸成為歐美、日本地區制藥研發產業鏈中的關鍵一環,承擔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新藥開發工作。其中90%以上CRO企業分布在歐美,服務范圍覆蓋了臨床前和臨床試驗新藥研發的各個階段。
CRO的高度專業化,可以幫助藥企縮短30%的研發時間,提高收入。一個年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的藥物早上市一個月,就能為藥企新增2億美元的潛在收入。
然而,彼時的中國,由于種種原因,幾乎沒有新藥研發的需求。
新藥研發風險巨大,通常耗時12——15年,動輒10億美元以上的投入,成功率卻不足10%。對中國藥企而言,還要面對另一重風險:即便研制成功,也未必進得了《醫保目錄》。
面對種種不確定,中國藥企對研發新藥望而卻步。而中國又是藥品消費大國,相關部門為解決藥品緊缺問題,讓中國數千家藥企走上了合法仿制之路。
統計顯示,我國仿制藥高峰時期曾占批準藥品的97.4%。同一品種仿制藥,在藥效上中國尚不及印度。2009年中國進入世衛組織采購目錄的品種數量為6個,印度則是194個。
懸殊差距的背后,是中國仿制藥因研發技術和態度問題導致的質量不達標。世衛組織采購的藥大部分用于非洲,由此坊間一直流傳著一個段子,說“中國的國產藥連非洲難民都不吃”。
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認證管理中心李正奇處長曾撰文稱:國產仿制藥總體質量比原研藥相差甚遠,有的甚至是安全的無效藥。
也因此,中國至今沒有誕生一個世界級的藥物品牌,這與藥品消費大國、生產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
在這樣一個國度,能產生商業化的新藥研發服務行業嗎?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業界眼里,這都是天方夜譚。
2000年,這種尷尬被33歲的李革打破。
彼時的李革,在中國并不被了解,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他已在業界嶄露頭角。
李革是北京大學高材生,1989年從化學系畢業后,在多個留學選項中他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有機化學博士期間,李革與導師共同發明了“標記的組合化學技術”,并由此發現了多種藥物前體化合物。
作為新藥研發的重要環節,這一成果讓他們順利拿到風險投資,隨后一起創辦了組合化學公司Pharmacopeia。李革擔任科研和管理職位,并主導了多項與美國各大制藥公司的合作項目。1995年,Pharmacopeia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
此間,李革在新藥研發和商業化運作上獲得了第一筆寶貴的經驗積累。但冥冥中李革感到,他的人生并沒有真正開始。
1999年,他應母校邀請回國訪問。國退民進政策下正在崛起的中國醫藥市場讓他看到了機會。
李革判斷,中國入世在即,在國際競爭和國內需求刺激下,新藥研發必被提上日程。且中國人力資源成本較低,高校和科研院所臥虎藏龍,他們并不缺技術和頭腦,只缺發揮才華的平臺和好的機制。
此時的李革內心還埋藏著另外一種情結:“小分子藥(化學合成藥)通常被稱為‘西藥’,這是不公平的。不論從市場角度還是出于振興民族藥業考慮,都應該從‘西藥中國化開始’”。
一系列思考之下,李革決定提早下手,回國做新藥開發。
第二年注冊藥明康德新藥開發公司后,籌建化學實驗室的過程中,李革感到了絲絲涼意。
化學實驗室需要專業通風櫥,他們在國內找了一圈卻找不到生產廠家,最終不得不自己設計圖紙定制生產。
凡此種種境況讓李革明白,國內新藥研發的底子比他想像的還要薄。李革很無奈,“突然間我感到特別茫然,不知道業務方向該怎么走。”
前路不明中,一個無意之舉,讓李革有了意外收獲。
當年底在一次國內航班上,李革畫了20個化學藥物模板分子,讓實驗室人員試著合成。
這種模板分子相當于建房時的主體框架。由于是新藥研發的基礎,大型藥企對此需求很大。
李革帶著合成結果找到一家美國藥企,對方十分震驚:這個產品居然能大幅度提高他們的研發速度,降低研發成本。
由此,李革敲開了雙方合作之門。
這次成功讓敏銳的李革意識到了新商機——新藥研發外包服務。藥明康德由獨立開發新藥公司,變為承接制藥企業新藥研發業務的服務公司。
這一轉,李革開了本土CRO行業之先,被媒體稱為中國醫藥研發外包產業第一人。
如李革所料,公司成立后,并不受國內藥企待見。因理念、價格等多因素影響,國內藥企沒有意識到藥明康德的價值,在新藥研發上仍沿襲老路,自己從頭做起,耗費巨大的財力、人力。
對此,1997年就進入中國的全球CRO巨頭昆泰醫藥也感同身受,其中國區負責人說,“在中國的18年發展歷程中,頭12年國內創新藥研發極少,沒有與我們合作。”
但李革堅信,中國總會有一天需要藥明康德。且這也絲毫不影響藥明康德首先成為國際化服務公司,它要“在中國服務世界”。
以此為路徑,藥明康德一邊廣攬國內外人才,布局軟硬件設施,建立從化學合成到原料藥生產、藥物安全評價等一整套服務體系,一邊大力拓展國際市場,以較低的價格提供最好的服務。
到2005年,藥明康德化學服務規模達到全球第一,為80多家大型制藥企業提供化學藥研發服務,客戶中包括諾華、輝瑞、禮來等9家世界排名前十的制藥企業。
因藥明康德提供的服務性價比高、出成果快,這些制藥巨頭們對其贊賞有嘉:美國禮來公司在其上千家供應商中,將“全球供應商獎”頒給了藥明康德;諾華制藥授予藥明康德“特別成就獎”;基因泰克則把藥明康德視為“杰出戰略合作伙伴”。
帶著一系列美譽、豪華的客戶陣容、超過2000名員工的規模實力,藥明康德于2007年8月在美國紐約交易所閃耀上市,當天,漲幅超過40%,總市值超過10億美元。
作為首個登陸紐交所靠頭腦服務的中國公司,藥明康德現象引發紐交所新一輪中概股投資潮。
上市后的藥明康德成了明星企業,大量外國CRO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尋求出路,上門求“賣身”。李革選擇了美國AppTec公司。
AppTec有400多名員工,提供生物制劑與醫療器械領域的研發、測試和生產服務,這正是藥明康德缺少的。合并后,兩家公司的業務范圍和專業技術完美互補,藥明康德完成了在化學醫藥、生物制藥及醫療儀器領域的服務全覆蓋。
這項收購藥明康德支付了1.51億美元現金,并承擔對方1170萬美元債務。美國彭博社報道稱,這是繼聯想收購IBM后,最大的中國企業在美并購案。
而這,只是李革布局中的一小步,隨著其對產業鏈上下游的接連并購,李革塑造了一個不同意義的顛覆性CRO公司。
對藥企客戶而言,在藥明康德的平臺上可以通過產業資源配置實現高質、高效的新藥研發、生產、上市。
對中國用藥患者而言,通過藥明康德可以提早用到進口新藥。由于中國實行特殊的進口藥審批制度,一種國外新藥需要在中國人身上再做一次臨床試驗,使國內患者用上國外新藥的時間至少要延后5年以上,有甚者長達十幾年。
“這對中國老百姓的健康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李革表示:“藥明康德的技術和能力平臺可以提供更創新的模式,讓國際間的創新研發成果可在中國和美國同時進行申報,使得西藥進入中國的市場不要太晚。”
同時得到福音的還有醫藥研發界的創業者,藥明康德可以讓他們離夢想更近。
藥明康德為國內外有研發能力卻不具備研發條件的團隊甚至個人提供一站式平臺,任何人、任何公司,哪怕只有一個想法,也有可能借助這一平臺實現夢想。
在李革看來,一個行業要想增加創新的結果,就必須增加創新的活力。
傳統式研發各自為戰,把大量時間和成本耗在了基礎設施、實驗室和資源配置上,并沒有充分利用科研人員的專長。
在一體化平臺上,與醫藥研發相關的各種資源特別是技術人才得以優化整合,既降低了創新門檻,又提高了新藥誕生的機會,更利于統一行業標準和成果轉化。
美國一家僅有兩名員工的小型創業公司就借助藥明康德實現了價值轉化。其主攻罕見病研究,藥明康德利用資源優勢在18個月內完成了創始人設計的一系列實驗,獲取的數據幫助這家創業公司以1.3億美元的價格被其他公司收購。
換個角度看,如果這家創業公司也是李革眼中的菜,那么李革也會毫不猶豫的將其收入囊中或以風投的身份參與。這是藥明康德構建全球尖端技術能力的一條捷徑,也是在全球CRO行業越來越同質化、競爭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藥明康德樹起差異化壁壘的不二之選。
對此藥明康德已經有了成功嘗試。首期公司出資5000萬美元建立的風投基金,投了16家公司,其中4家在美國上市,2家被收購,包括國內天演醫藥、華領醫藥、丹諾醫藥等企業。
一邊在立足長遠精心布局,一邊李革也開始收獲研發碩果。
到2015年藥明康德誕生15年,恰好是新藥研發的一個周期,藥明康德早年的努力已見成效,這一年美國批準的45個新藥中,有33個來自藥明康德的合作伙伴。
獨闖天下十幾年,雖成就令業界矚目,但相較回國創業的初衷,李革更期待能為中國的新藥研發做點什么。
等到這一天,李革用了13年。背后是中國本土對新藥研發態度的轉變。
這種轉變來自兩種力量。國內自2009年后,藥監部門基于“十一五”長遠規劃,提高了對藥物注冊的要求,大量藥企不得不向CRO公司尋求幫助。
國際上,制藥巨頭和大量CRO公司瞄準中國人力資源優勢和市場需求,將藥物研發中心向中國轉移。
內外刺激下,中國的新藥開發局面被激活,CRO漸漸進入越來越多藥企的視野。繼藥明康德后成立的博濟、美迪西等一眾中國本土CRO企業,均感到了市場暖意。
2013年,藥明康德迎來本土訂單——浙江醫藥和美國Ambrx公司合作開發一種治療腫瘤的抗體藥物。藥明康德為其提供包括臨床前實驗、生產、安全性評價以及最終的臨床研究等工作。
以此為開端,譽衡藥業、眾生藥業、正大天晴、廣生堂、華潤醫藥等國內藥企也緊隨其后,陸續與藥明康德攜手,共同就新藥臨床前研發展開合作。兩年后,本土訂單已占藥明康德營收的近18%。
一方面藥明康德在用自己的技術助力中國藥企研發,另一方面,其也在用國際影響力將國外制藥巨頭的核心技術引入中國。
2016年3月藥明康德宣布與全球最大制藥企業禮來合作,共同在中國開發、生產及商業化一款全球首創的口服降血脂新藥,引起業界關注。
過去數十年間,盡管全球頂尖藥企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但出于技術保護,巨頭們在中國進行的研發大都是在國外已經成熟甚至是已被淘汰的項目。像禮來這樣一開始就把如此重要的創新藥拿到中國來研發尚屬首次。
業界有評論稱,是中國醫藥研發制度改革吸引來了對方的合作。但不可否認的是,此前雙方超過10年、累計近千項的藥物研發及生產合作歷史,也應是此次合作的重要基礎。
隨著藥明康德國際化、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其開放式全產業鏈平臺的示范引領效應也愈加明顯,不僅帶動了國內新藥研發服務產業和上下游相關企業加速成長,也為中國培養和儲備了大量與國際接軌的科技人才,成為業界公認的“黃埔軍校”。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CRO業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創新藥物研發中心。有媒體報道,中國已超越印度,成為世界醫藥研發服務業的首選地。
縱橫捭闔17年,國際國內并舉,從650平米實驗室到57家境內外控股子公司、3家分公司,2015年CRO業務全球第十位,藥明康德儼然成了全球行業新晉大鱷。
面對這樣的藥明康德,威名赫赫的美國藥物研發公司查爾斯河(CRL)心里不是個滋味。
早在2010年,覬覦中國市場已久的查爾斯河曾計劃以16億美元收購藥明康德。后者寄望借助收購交易實現業務互補、完善產業鏈。
但四個月后查爾斯河毀約,公開理由是股東質疑收購價格過高,對藥明康德的一體化平臺前景不看好。
如今看來,這是藥明康德之幸,也是中國醫藥界之幸,在國際醫藥界,中國的話語權仍然存在。
化險為夷后不斷進階的藥明康德向全球老大的挑戰還遠沒有結束,資本市場持續不斷的動作,又將李革推向輿論巔峰。
去年7月14日,證監會網站披露藥明康德招股說明書。這是其2015年自紐交所下市后打出的第三張回歸組合牌。今年3月27日,證監會網站的信息表明,藥明康德已成功過會。
和大多數下市企業一樣,藥明康德決定下市也是因為在紐交所沒有受到應有禮遇。根源在于華爾街的投資者對李革超越傳統CRO的平臺模式不買賬,投資人更注重短期業績,看好單純接合同訂單、現金流有保障的業務模式。2015年3月當藥明康德公布大型戰略投資計劃后,股價應聲跌了20%。
從數據上與國內創業板的同行小弟泰格醫藥相比,在紐交所的老大哥藥明康德的確受了慢待。藥明康德2014年營收和凈利潤是泰格醫藥的5—6倍,市值卻只是后者的1.2倍。
這讓李革很受傷。
“我對這個結果感到非常失望。我們想要保持創新,卻不能得到正向的激勵。因此我覺得是時候下市了。下市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大膽地投資平臺建設,更加靈活地把握新興機會。”
事實上,這一時期的紐交所有20多家中概股啟動了下市進程。但到當年下半年,A股爆發股災,大部分中概股又放緩了該計劃,藥明康德則表現出義無返顧的決絕。且從最初宣布到最終完成,僅用了四個月時間,下市成本約33億美元。
下市后的藥明康德新股東中不乏明星機構,博裕資本、淡馬錫、匯橋資本、中國平安、浦銀國際、云鋒基金、紅杉資本等均現身其中。藥明康德找到了“回娘家”的踏實感。
事后外界慢慢發現,原來藥明康德并非簡單的回歸A股,而是打出了一系列高明牌。
其先是將旗下以化藥臨床前CRO為主營業務的合全藥業在新三板掛牌,并一舉成為新三板醫藥股中的翹楚,總市值達172億元,母公司藥明康德擁有其近80%股份。
兩年后的2017年6月13日,藥明生物登陸港交所。其主要提供一體化生物制劑研發服務。在中國和全球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48%、1.8%,排名分別為第一、第五。上佳的數據引發投資者熱捧,上市一個月后市值418億港元(約合361億元人民幣)。
而A股部分,除了合全藥業以及提供臨床前CRO外,藥明康德還提供臨床期相關服務。招股書顯示,藥明康德預計發行價21.6元/股,計劃募集資金總額約為22.51億元,融資將用于擴大產能,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業務需要。
從當下的結果看,藥明康德的回歸算不上一帆風順。5月1日晚間,藥明康德披露的IPO發行結果顯示,網上投資者放棄認購數量為32.28萬股;網下投資者放棄認購數量為5634股;累計棄購數量為32.84萬股,棄購金額高達709.4萬元。
不過,有證券機構估算,就發行市盈率與行業市盈率比較而言,藥明康德發行價相對行業市盈率存在較大折價,預計上市后上漲空間較大。
即便按藥明康德發行價計算,李革與“藥明康德系”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包括合全藥業(832159.OC)和藥明生物(02269.HK),總市值也接近千億人民幣,而全球CRO老大昆泰醫藥上市主體,市值也不過217億美元(5月2日數據)。
作為中國一個行業的拓荒者,李革成功了。作為全球行業的顛覆者,李革也已見到曙光。在中國從仿制藥大市場向新藥研發努力前進的過程中,他和藥明康德所提供的,或許遠不止一家總市值千億的集團化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