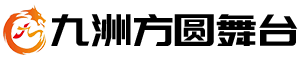畢井泉,在食藥監局任職只有短短4年的時間,卻通過一系列改革,“開啟中國醫藥創新時代”。作為操刀過“722事件”、“44號文”、“一致性評價”的改革者,其勢必對于當下生物醫藥面臨的局面有著深刻的理解。
日前,在第十五屆健康中國論壇上,畢井泉也指出了癥結所在——
鼓勵創新是當前的主要矛盾。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需要增加有關產業和領域投資,加快發展,提振市場信心,改善市場預期。
誠然,這一輪始于2021年下半年的資本寒冬,與資本投機、美元加息、地緣政治等因素強相關,但更多的問題,或許還要從政策端尋起。
正如畢井泉所說,鼓勵藥企創新,離不開政策的扶持;改善市場預期,同樣離不開政策的引導。
在中國,很多領域的徹底改變,需要內部的“卷力”和外部的“倒逼”,也需要領導的殷切關懷,需要部委的高度重視。何況,還是生物醫藥這樣一個監管深度介入、對政策高度敏感的行業。
寒冬何時結束,不得而知。無論如何,請不要讓生物醫藥在寒冬里徹底沉淪。
/ 01 /
拯救投融資
寒冬摧殘的,是所有人的信心。
2019年至2021年無疑是醫藥行業蓬勃發展的三年,但是基本面增長得快,市場預期膨脹得更快,加之新冠疫情催生的一系列新需求干擾了人們的判斷,最終導致整個行業出現了產能大擴張,遠遠超過了市場的需要。
而資源在短期內的過度涌入,導致單藥研發成本飆升而單藥回報預期滑落,一升一降之下,投入產出預期惡化,內卷競爭壓力凸顯。
其中,產業投機的存在導致行業中的一些超額收益消失,美聯儲加息后創新藥融資斷崖式下跌疊加新冠相關需求驟降,更凸顯了行業的產能過剩;而監管推動的降價、創新藥出海不順,更是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行業的盈利預期,泡沫破裂。
2022年起創新熱潮再度陷入大冰凍。
二級市場跌跌不休,無論A股還是港股,當下都處于估值底部。這也使得絕大多數藥企失去了融資窗口。
而港股18A自2018年運行以來,截至2023年年底,共有63家企業通過此規則在港股IPO。
但是,經過過去兩年的寒冬洗禮,IPO募資額和IPO數量雙雙跌至冰點,牛市的時候年募資額在350億港元左右,熊市只有35億港元左右。
科創板IPO形勢也不容樂觀。去年下半年,市場甚至流傳出科創板第五套標準新申報企業已經暫停使用的消息。
某種程度上,喪失融資功能的IPO通道,已經偏離了其使命軌道。
一級市場更是上演“融資懸崖”。根據醫藥魔方數據,中國創新藥一級市場融資金額2020年為869億元、2021年為877億元,2022年下降到433億元,2023年進一步降為309億元,兩年累計下降65%。
這讓極度依賴資本的生物醫藥行業,陷入了一個超級“向下”螺旋。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生物醫藥領域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方向,但在這個過程中,投資者也面臨著一些困惑和難題。最消磨人心的是,投資在一個周期里,退出在另一個周期里。
盡管投融資是市場化行為,但依舊需要“有形的手”從中協調。有投資機構也直言,需要建立一個長期的資本生態系統,支持機構進行判斷、周期匹配和風險承受。
某種程度上,拯救生物醫藥投融資信心,刻不容緩。
正如畢井泉所說,生物醫藥融資大幅度下降意味著很多生物醫藥企業面臨嚴重的資金困難。生物醫藥創新是一個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漫長過程,如果不能融入新的資金支撐實驗室研究、動物試驗、人體一二三期臨床試驗,生物醫藥的創新可能戛然而止。
對此,他建議應當研究:
支持符合科創板第五套標準的創新藥企業上市;
鼓勵龍頭企業增資擴股;
開展企業并購;
恢復二級市場的融資功能;
鼓勵地方政府設立生物醫藥母基金;
支持生物醫藥早期投資。
/ 02 /
既要又要
都說醫藥是一個永遠朝陽的行業,但與民生緊密相關的特性,決定著它是一個監管深度介入、對政策高度敏感的行業。
一面需要鼓勵創新,實現生物醫藥產業從大到強;另一面需要“約束”創新,因為創新藥的價格,決定著老百姓看病就醫的負擔,也決定著行業的規模上限。
本質上,這是一個既要又要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過去幾年的政策中,既能看到創新藥審批改革、突破性藥物審評這種“鼓勵型”政策,也能看到DRGs、醫保談判、臨床監管收緊這種“約束性”政策。
具體到藥企們又愛又恨的醫保談判,不進醫保,銷售難行,而進醫保,一旦被靈魂砍價,可能很難以價換量。市場更是普遍擔憂,隨著帶量采購產品范圍邊界被持續打破,創新藥也沒了下半場。
過去幾年,在控費、藥企內卷的背景下,大家最熟知的莫過于國產PD-1大降價的故事。固然,低價能在很大程度上惠及更多患者,但創新藥行業并不能“唯低價論”。過低的藥價反而會反噬創新生態,影響藥企研發、出海等戰略的順利推進。
眾所周知,創新藥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一款成功上市的創新藥,成本收回的周期甚至長達10年以上。
人民日報此前也曾發表評論稱,醫保談判是與企業的協商,決不是“價格越低越好”的隨意砍價,而是為參保人爭取最大利益,同時賦能醫藥行業高質量發展。
這也是一個既要又要的問題。
當然,對于創新的支持,監管已經拿出了誠意。近兩年,醫保談判越發溫和,具體細則也在逐漸修正的更加科學和合理,政策對于創新藥企及產品的支持也肉眼可見。
但這對于重拾市場信心,或許還不夠。
對此,畢井泉建議,應當研究改革創新藥價格形成機制。創新藥定價,涉及鼓勵創新、專利市場獨占、投資人回報、醫保資金支付、患者可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與之相關的建議,還包括研究取消創新藥進入醫院的各種限制,取消醫院藥事委員會批準采購新藥的規定,提高醫療服務價格,推進醫藥分開。
這些建議,本質是調整利益格局。如果站在這個層面,再去理解這輪史上最強醫藥反腐,一切豁然開朗。
藥企的成長與生態環境相輔相成。中國生物醫藥的長遠發展,需要更多企業走出內卷怪圈,也需要政策層面給予更多支持,持續探索。比如在“價格保護”方面做得更好。
事實上,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地區,對于高臨床價值創新藥都有著符合其國情的價格保護政策。即使是在嚴格控制藥價的法國,為了推動創新、促進投資和出口,三年前法國也對部分藥價管控條款進行了大幅修改。
回到國內來說,探索符合國情的價格保護機制非常關鍵。
中辦國辦日前印發的《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中提出,依照有關規定允許生物醫藥新產品參照國際同類藥品定價。
盡管方案內容尚過于簡略,但這無疑是一個讓業界充滿希望與期待的改革方向。
/ 03 /
預期管理
從2015年國內推進深度醫改以來,宏觀和微觀視角看到的感受截然不同:宏觀來看,醫保結余8.24萬億,基金平穩運行,生物醫藥底層邏輯依舊穩健,持續增長;微觀來看,行業高度變幻,滄海桑田,到處變遷。
以A股、港股的TOP10藥企為例,2015年的10家藥企在2023年只有恒瑞醫藥1家留存,其他藥企全部掉出前10。
行業格局變動之大令人印象深刻,頭部公司的核心價值驅動,也已轉向創新、國際化和升級。
由此可見,醫改政策對行業生態的重塑作用是驚人的。不僅政策能夠塑造行業生態,行業特性也能左右政策的推廣效果。
過去幾十年紛繁復雜的醫改歷史中,但凡有顯著持久成效的政策,比如藥監規范監管、醫保全民擴圍、扶持創新發展,無一不是順應了醫藥的底層邏輯,即人們對生命與健康的普遍性珍視;而那些不太契合行業底層特性的,比如10年前強推低價基藥和基層診療等等,最終都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這需要長遠規劃、系統推動,處理好長遠與短期、整體和局部、國內和國外的關系。
如果用畢井泉的話來說,那就是,在生物醫藥領域,我們尤其需要增強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一致性。按照把生物醫藥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求,對涉及生物醫藥的研發、注冊、生產、使用和支付各個環節進行“取向一致性”評估,及時調整取向不一致的政策,確保同向發力、全鏈條支持,幫助這個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資本寒冬中走出來。
生物醫藥行業需要一個積極正向、支持性強的生態系統。無論是研發能力、市場接受度、資金支持、法規容忍度還是風險控制與商業機制,都需要監管做好鼓勵創新的預期管理、政策支持。
當然,生物醫藥絕非一個可以僅靠政策來發展的行業。如果說,上一輪的創新浪潮,是在資本、產業和監管三方面的共振下誕生的。那么,要順利渡過此次寒冬,讓生物醫藥重新煥發生機,更是應當如此。
所有行業參與者也要深刻反思,在上一個周期,生物醫藥產業的系統在運作過程中暴露了哪些問題與不足,來為下一個周期做好準備。
寒冬之中,有人只看到了風險,有人看到了風險背后的機遇。當我們跳出短期的不確定性,或許會發現未來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好,但也不會如想象中那么糟。
因為,驅動醫藥行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類對健康和生活質量的追求,在這個本質需求的基礎上,醫藥行業會不斷地被賦予各種內涵和表現形式。
但只要人類在進步,醫療健康需求也會與時俱進。
換句話說,不管我們是否看得見,能否抓得住,創新大勢都在那里,在磅礴恢弘的運動中,緩慢而深刻地重塑著行業與生態。
誰都沒有理由,在寒冬里繼續沉淪。
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煜森資本立場,歡迎在留言區交流補充。如需轉載,請注明文章作者和來源。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在本平臺留言。